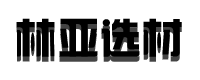在那次事发后那么多年,我丝毫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不安或慌张——我知道那是本应发生的。无由的聒噪终会平息。那次事件后,我心头上的一个结仿佛被打开了。事情的来龙去脉,且听我娓娓道来。
二十年前的一天,那是个令人满意的上午,阳光平坦的铺洒了整座城市,鸟儿的叫声在屋顶塔尖互相应和。这种天气出门散步再合适不过了——可恶要去上那该死的课。高中毕业后,家人便托关系让我进入了这所号称是“贵族学校”的坎特公学。为了摆脱他们长年对我无休止的束缚,我便只身一人来到英国的这所“贵族学校”。这天的好心情被不留情的践踏了,我还没出宿舍门,便听见布鲁戴尔雷那个家伙聒噪的声音。
“嘿!伙计!为什么没去参加派对?好多漂亮姑娘!”
英国人素来都喜欢装腔作势,罗伯特老师身上将布鲁戴尔雷运用这招的精熟体现得不留余地。揭开布鲁戴尔雷之流的皮囊,便可见腐烂的肉身。每晚花天酒地,灯红酒绿的生活,有时甚至在宿舍中都能听见他们宿舍中的嘈杂声。我有时怒不可言,可语言又不太通,从我嘴巴里说出的英语总是慢条斯理的,慢条斯理只会让那畜生更加嚣张跋扈。
我推开门,他身着蓝白条纹的衬衣,藏青色尼龙布料的裤子,头顶着一团棕黄的绻发,像极了用来清洗的钢丝球。日复一日的狂欢使得英国佬原有的黑眼圈越发的明显,颧骨下面的脸颊凹陷下去,一看便知是长时间吸食大麻所致,嘴唇却红的吓人。他一手插在口袋里,一只肩膀耷拉下来,一只手则夹着半截雪茄。脚上皮靴有规律地跺着地板。
他像极了猴子屁股的嘴里仍然像在发生了一场争吵,喋喋不休地在你耳边萦绕。不管我对他有多么厌恶,多么看不惯他,我都尽量不溢于言表——我不希望被别人发现——别人大概率的只会听信于与其同种族的人的话。我这种独在异乡的游子只好扼守着我的慈悲。可一早上便看见他,心中难免不快。于是我便盯着脚下的路,很快从他身边走过。两秒之后,他和他的同伴发出了一身讪笑——那是一种极度的自我感的膨胀——这一定是针对我的。
到了教室之后,罗伯特老师已经在上课了。
“先生,你迟到了。”
“是的,罗伯特先生,很抱歉。”
“下次尽量早点,我听说你们中国人经常迟到。”
我没有说话,为了表示对这段话的抗议,我的膝盖带动身体抖了几下。
“先入座。”
几分钟之后,布鲁戴尔雷和他那一伙到了。
“非常抱歉,罗伯特先生。我为我们的迟到而向您道歉。”
“哦!又是你!你这个星期已经迟到三次了吧,加上这次。不过,看在你一直诚恳地向我致歉的份上,我再一次原谅你,布鲁戴尔雷先生和你的伙伴。”
“十分感谢。”他的喉管中发出的这几个字像他故意憋出来的。
“入座吧。”
我十分厌恶虚伪,特别是加在他身上的虚伪,他身上的虚伪已经不足以用语言来形容了,那种谄媚的样子好像是他在演练千遍过后而达到的一种纯熟的境界,脸上那种因自己的机警而透露出来的笑意释放他内心的邪恶,不过就是一瞬间,很快,他就恢复到原先的那副假面上。
罗伯特老师写了一道题,我很快写出了这道题的完整过程,并举手向他示意。罗伯特老师看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课后,那个浑蛋走到我身旁,没向我示意就抄走了我的稿纸,并说“哪抄的?哈哈!”
“喂!伙计!我听说附近的一个工地好像发现了宝贝,我们今晚去看看,嗯?”
“真的吗?太棒了!你真够mason的!”他跳了好高,生怕有人会发现不了他的存在,于是他又跳了一次。
晚上我和布鲁戴尔雷偷偷地翻过了那堵破败不堪的围墙,上了大街。
“你说的宝贝已经被人发现了,肯定会被人拿走呀!”
“我说可能有宝贝,你要没兴趣,咱就回去吧!”
“不不,回去多没意思,不过,我们怎么找?”
我拿出了一把小锄头和一把胶枪。
“这胶枪用来干嘛?”
“过会你就知道了。”
“怎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?你闻到没?”
“嗯?有吗?你肯定被吓出幻觉来了。”
“怎么可能?!这有什么怕的?”
“你说如果我现在把你杀了,罗伯特老师找得到你吗?”说完,我就笑了起来。
“别开玩笑了,兄弟。”布鲁戴尔雷的脸变得苍白起来,嘴唇更加血红,像一个僵尸。
施工的场地里面的工人们都下工了。晚上,只有一轮凄惨的明月挂在天上,风吹过工地上的泥沙发出“呼呼”的声音,除了布鲁戴尔雷和我,其余都安静得出奇。惨白的月光铺照在灰色的水泥上,一堆堆的小沙丘,尤其像一个火葬场。
我们从栅栏的缝隙中钻了进去,我找到一大桶未干的水泥旁。趁他蹲下来的同时,把沾有大剂量高浓度乙醚的布死死地蒙住了他的脸,很快,他就浑身无力,没发出任何声音。我拿出胶枪,把他的眼睛,鼻子,嘴等全身上下有洞的地方都填充满胶水,再抄出那把头已经被我磨得极尖锐的锄头放在一旁。用一个簸箕似的容器垫在他的头颅底下,然后用锄头狠命地砸,把对他的所有怨气都灌输其中。很快,脑浆和血混合的糊状物质就流满了整个容器,他的头部早已稀烂,所有器官和皮肉交错在一起,唯有一颗辛未受到破坏的眼球镶嵌在上面。
我并没有像别的杀人犯一样很慌乱地逃离,反之,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安稳,心平静得像一面湖水,内心似乎某处通畅了。月亮在我头顶,这时候真该配上一曲《小夜曲》。我趁没有人经过时再次走上大街,每一步都走得比以往更安稳。那晚我也睡了个及其安稳的觉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
第二天警察来询问情况,罗伯特老师出面与其交谈。
“他是个善良的人,真心地希望你们能找到他。”
............
很多年以后,作为唯一知道布鲁戴尔雷去处的人,我再一次路过那片曾经施工的工地。昔日的工地现早已高楼林立,灯火通明。而我脚下,是坚实的水泥地。
(全文完)